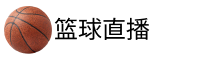一場看似“低調”但意義重大的變革。
據財新報道,三名知情人士確認:鴻蒙智行旗下智界、尚界和享界正由合作車企籌備建設品牌專屬銷售網絡。
這意味著,三個品牌車型的銷售與售后將不再由華為主導,轉為由合作車企各自負責。

華為已經針對汽車業務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,還包括余承東卸任車BU董事長、車BU獨立運營為“引望”公司、在智能汽車領域尋求更靈活的市場化運作方式等。
這些動作的背后,可能是華為的戰略回歸,重拾起初入進軍汽車行業時的既定戰略角色。
2013年,華為便成立車聯網業務部,推出了車載模塊產品,但真正加速入局汽車行業,是2018年。消費業務的斷崖式下跌,迫使華為提升汽車業務的重要性,尋找新的營收增長引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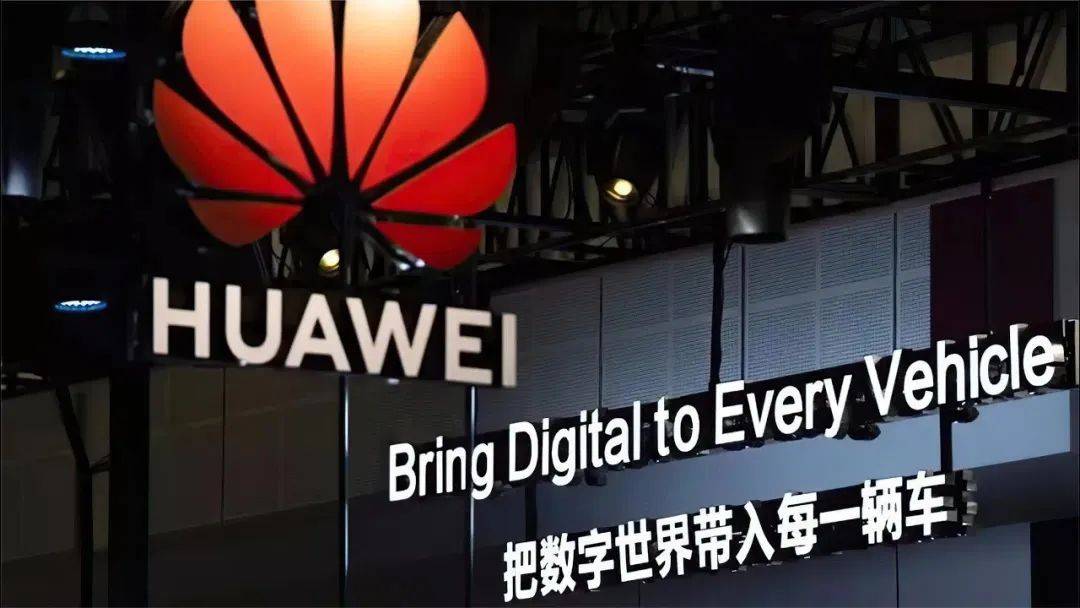
彼時汽車行業也在經歷深刻變革,智能電動化正在改變著汽車行業的格局。
中國也借由這場時代機遇,尋求從汽車大國蛻變為汽車強國,華為也尋找到自己的機會,成為中國的汽車零部件供應Tier1巨頭。
華為的決策依據很清晰,汽車行業技術密集、資金密集和長鏈條的特性決定了,每一個汽車強國,除了家喻戶曉的汽車品牌外,還必有零部件供應的巨頭,共同維系汽本土汽車行業的創新活力與長遠發展。

電裝之于日本,法雷奧之于法國,麥格納、德爾福等之于北美,博世、大陸之于德國,皆是珠玉在前。
尤其博世集團,業務涵蓋汽車、智能交通、工業技術、消費品和能源等行業,有“世界隱形冠軍”之譽。

中國不缺少規模龐大的汽車廠商,但對比之下,零部件供應商的身板就單薄得多。
前華為智能汽車解決方案事業部(BU)總裁王軍就直言:中國(汽車零部件行業)的Tier1、Tier2(一級、二級供應商)太分散了,沒有巨頭。
這種過于零散的格局就造成了,中國汽車零部件供應商難以聚集成規模的資金,不易研發、落地超前沿的技術。
零部件供應巨頭生態位的缺少,已經在掣肘中國汽車的產業升級。中國華麗轉身為汽車強國的前夜,需要有一股力量來打破頭重腳輕的產業格局。

恰好華為具備這個能力,汽車行業這場智能電動化變革需要的底層能力,正與華為所擅長的ICT技術是相通的。
例如,智能駕駛輔助會用到的感知硬件激光雷達,華為可從自身的光網絡產品線孵化出來。還有高清攝像頭和視覺感知方面,華為入局汽車行業前便有專門的機器視覺團隊。
與其說華為決定進軍汽車行業,倒不如講,這是一場智能電動汽車與華為的雙向奔赴。

華為參與汽車行業有三種方式:零部件模式,作為一級或二級零部件供應商,為車企提零部件;HI(Huawei Inside)模式,與車企合作,提供全棧技術支持;鴻蒙智行(智選車)模式,深度參與產品設計和品牌打造。
參與度更克制的零部件與HI模式是華為早期更被車企門接受的途徑,客觀因素是華為與車企間需要建立信任。
另一項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素,則是零部件和HI模式也更為契合華為“不造車”的超級供應商定位。
華為盡量避免觸及自身不擅長的機械制造,而是專注于做智能網聯電動車領域的供應商,并且只做電子相關的增量部件。所以華為帶著智能網聯電動車標簽首次出圈的載體,是采用HI模式的北汽極狐 阿爾法S HI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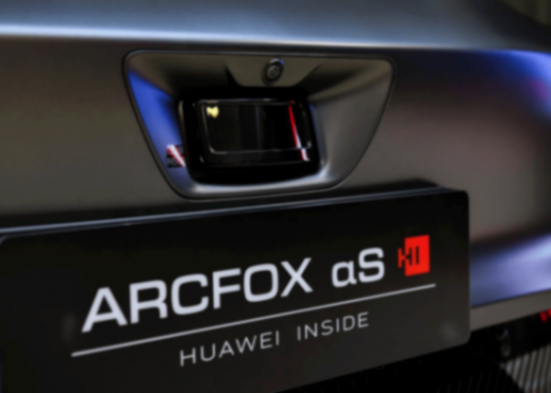
但華為智駕聲名鵲起,零部件與HI模式下的汽車業務卻難收獲與之相匹配的業務增長。于是,鴻蒙智行開始發力。
鴻蒙智行前身是華為終端與賽力斯聯手創建的智選車模式。該模式下,產品設計、定義、制造、銷售、服務均由華為把控。
智選車模式首次展現驚人實力,是2023年改款問界M7的翻紅。一臺發布不到一年且毫無市場熱度的冷門車型,卻能在華為主導下,僅以改款形式,翻紅爆單,這在汽車行業極其罕見。

電子相關的技術實力外,通過智選車模式高度的話語權掌握,華為還將自身的“跨部門協同”能力導入到汽車行業的競爭中。
2023年的AEB紛爭提供了一個觀察華為組織能力的絕佳視角,彼時智能駕駛尚未在消費端真正影響用戶決策,反而是主動安全更易被大眾認可。
華為敏銳捕捉到了這一市場信息,并快速調整研發資源,導向AEB功能,率先推出了側向AEB、全向AEB等用戶易感知的AEB功能。

AEB功能并不新奇,相比智能駕駛,也不高深復雜,但易感知的AEB功能對用戶訴求的迎合,為營銷帶來的助力,是意義非凡的。實際上,很多用戶沖著AEB功能購車,但最后更喜歡的反而是ADS智能駕駛。
這是可以寫進商業教材的經典案例,而背后,則是華為重視營銷與產品的相關性,并擁有將市場、研發、制造、銷售等多部門聯合起來的的整合能力。
鴻蒙智行也交出了亮眼的成績單,2024年交付44956輛,截至2025年上半年,累計銷量已經突破80萬輛。

但鴻蒙智行也有隱患,包括與上汽合作的尚界,華為已經組齊了問界、智界、享界、尊界在內的龐大陣容。
一碗水要端平,如何協調不同品牌間的關系是個問題。不講寶貴的研發資源如何分配,單是有限的門店內該擺放哪個品牌的車子,就很頭疼。
與華為合作車企同樣也有自身孵化、定位相近的品牌,例如奇瑞在智界之外,還有星紀元品牌。這也牽扯出一個更嚴肅的矛盾,制造商與供應商的同位悖論。

智選車的合作模式,華為雖然仍在宣稱沒有造車,但實際上,車企的角色更貼近于代工制造。
大眾認知中,鴻蒙智行已經等同于華為汽車。而華為既是供應商,在制造商背后提供技術產品,同時也與一部分制造商高度綁定,參與競爭,邏輯上的可行性并不高。
這種制造商與供應商一體的模式,其實是垂直整合的一種。垂直整合模式也并不新鮮,汽車行業早期,通用、福特,以及快速發展期的豐田,都采用過垂直整合。

一個行業興起初期,技術路線、供應鏈成熟度、市場認可性都不確定,垂直整合模式可以高效掌控決策資源與研發標準。
比亞迪正是在新能源汽車發展初期,采用垂直整合模式,攥緊技術標準的同時,還可以降本增效,獲得了領先身位。智選車模式的發力,也是此般邏輯。
但隨著技術方向的確定、行業規模的擴大,垂直整合模式便逐漸失去競爭力。夏老師此前詳細解釋過:
在行業的不同發展階段,垂直整合與橫向集成各占效率優勢。在新興期,不確定性大,經驗少,模式未成型,以汽車制造商為龍頭的垂直整合效率較高,福特、通用就是這樣成功的。
到了成熟期,垂直體系成了累贅,剝離開有利于發揮各自的特長,說白了,長期競爭篩選出了最佳解決方案,也導致更高的同質化,技術的標準化令供應商專屬于一家車廠變得低效...
所以一旦行業進入成熟發展期,汽車廠家一般會選擇剝離出獨立的供應商,以尋求各自的高效、健康發展。
鴻蒙智行就存在著這樣不協調,一名華為合作車企人士就表示,車企是品牌所有方,也是零部件采購主體,鴻蒙智行負責銷售和售后服務有些“擰巴”。

當新能源汽車市場滲透率長期突破50%,智能化也愈發影響消費決策,與車企也已構建起合作機制,對于華為而言,汽車行業的競爭重點也從幾個產品“一城一地的得失”,轉為全面的生態爭奪。
車BU獨立運營為“引望”公司,智界、尚界和享界的銷售由合作車企負責,都是華為再次釋放“不造車”的信號。
鴻蒙智行“放權”后,不單華為可以輕裝上陣,廠家也持積極態度,智界產品總監就表示,“本周之后,智界可以全力向前奔跑!”。

另一個市場態勢是,HI模式也開始展現出不俗的生命力。ADS智駕與鴻蒙座艙助力,結合自身定位的調整,近期上市的嵐圖FREE+收獲了不錯的市場反饋。
猛士M817、深藍S09等產品也都以首批搭載華為ADS 4智能駕駛輔助系統和鴻蒙座艙作為產品記憶點。
這就如同之前廠家宣傳其產品時,會強調搭載了博世的One-Box解耦線控系統、天納克蒙諾的減震器、寧德時代的電芯等。

華為在國內市場和智能化領域甚至具備更強的號召力,最好的佐證,莫過于德系豪華品牌奧迪選擇與華為合作。
同時,HI模式的華為印記也在淡化,HUAWEI INSIDE不再出現出現在車尾,取而代之的是代表智能駕駕駛輔助功能的ADS標識,華為在擁抱更廣闊的天空。

更多廠家接納ADS智駕與鴻蒙座艙,不單會直接助力華為汽車業務的增長,也有利于生態互聯的搭建。
智能汽車被認為是下一代智能移動終端的重要代表之一,有望成為居住與工作場所之外的“第三空間”,勢必成為萬物互聯的重要載體。
手握滿血鴻蒙這樣的底層操作系統,配合上車率日高的鴻蒙座艙,華為是為數不多具備打通3C電子、智能汽車、智能家電間生態互聯的公司。
華為退了一步,讓渡鴻蒙智行的銷售和服務權力給合作廠家,但同時也在鎖定智能化超級供應商的身份,擁抱更廣闊的天空,掌握更重的話語權。